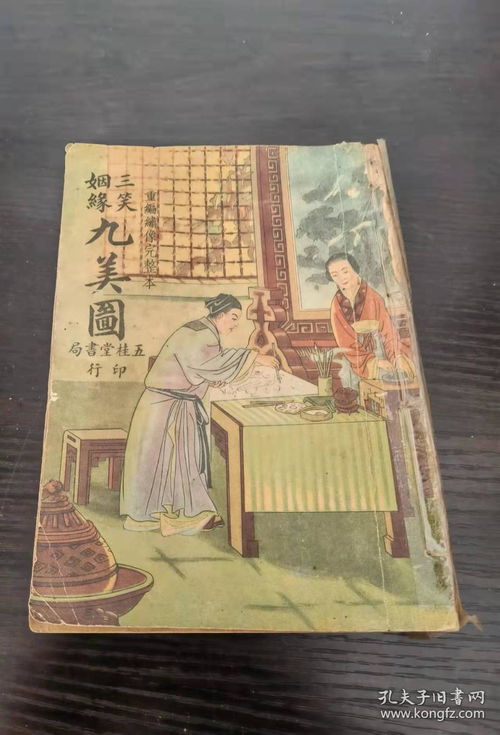姻缘神黑化之后残暴皇帝:我曾是掌管姻缘的神明
直到凡人窃取我的权柄,
将我贬入这污浊人间。
如今我坐上龙椅,
以凡人之躯践踏苍生,
却始终忘不掉那背叛的痛楚。
神座之下,血与烬——墨渊的暴政
冰冷的龙椅,金饰早已被暗红的血迹浸透,依旧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寒意,墨渊端坐其上,宽大的龙袍下摆垂落,遮掩了他脚下积起的尘埃与碎屑,他微微眯起眼,殿内光线昏暗,只有角落里几盏摇曳的烛火,映得他面容模糊,只余下一片深邃的、令人不安的阴影。
“启奏陛下,城外北麓,有‘妖孽’作乱,荼毒生灵,恳请圣裁。”一个奴才战战兢兢地跪伏在地,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。
墨渊没有立刻回应,他只是用那枚冰冷的、曾经象征着他神权的扳指,轻轻敲击着扶手,敲击声在死寂的大殿里格外清晰,一下,又一下,像是在丈量这座曾经由他守护、如今却充满怨恨的人间。
“妖孽?”他终于开口,声音低沉沙哑,不带一丝温度,“朕倒要看看,是何等孽障,竟敢在朕的脚下兴风作浪。”
“回禀陛下,那‘妖孽’通体漆黑,能惑人心智,引人自残……”奴才继续禀报,试图说得详细些,却又被殿外隐约传来的厮杀声打断。
墨渊猛地站起,龙袍翻飞,带起一阵阴风,他几步走到高窗边,俯视着下方尸横遍野的战场,一方方残破的旗帜,散落的兵器,还有那些蜷缩在泥泞与血泊中的尸体,被活下来的溃兵粗略地堆叠在一起,远处,一座孤零零的山村燃起了大火,浓烟滚滚,与天边的血色残阳融为一体。
“又是北麓?”墨渊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暴戾,“告诉那些‘神使’,告诉他们所有‘神选之人’,告诉他们,人间的蝼蚁,也配染指神权?!”
他转过身,目光扫过跪伏在地的奴才,那眼神冰冷得能冻结血液。

“至于这北麓……”他缓缓抬起手,指尖凝聚起一股几乎凝成实质的、令人窒息的黑暗气息,“就让它化作焦土,连着那些‘妖孽’,连同所有敢于反抗的‘愚昧’,一起埋葬!”
黑暗气息在他指尖疯狂扭动,发出令人牙酸的嘶鸣,殿外的厮杀声似乎被这无声的命令所震慑,渐渐平息了下去,只留下死一般的寂静。
墨渊重新坐回龙椅,仿佛刚才那股几乎要将整个北麓都吞噬的毁灭之力,只是他无意识的流露,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,试图驱散那股在权柄中滋生的、日益膨胀的怨毒。
他记得,很久以前,他是司掌姻缘的神明,月下老人,见证人间无数痴男怨女的情丝,也曾洒下祝福的甘霖,那时的他,尚存一丝怜悯,一丝慈悲,直到那个“神使”出现,那个披着神圣外衣、实则野心勃勃的家伙,窃取了他本应属于他的、决定众生命运的权柄,一场无声的背叛,将他从神座上拉下,打入这污浊的人间。
他曾是神,他只是这腐朽人间的皇帝,一个被凡人册封、供奉的泥胎木偶,他夺回了权柄,踏着累累白骨,坐在了这至高无上的位置上,他以凡人之躯,行神明之事,践踏着脚下每一个渺小的、挣扎的灵魂。
他试图找回过去的荣光,却发现记忆早已蒙上了厚厚的尘埃,那些关于姻缘的美好传说,那些被他亲手缔结的良缘,都成了遥远而模糊的梦境,留在他心头的,只有被背叛的刺痛,只有对这虚假人间的刻骨仇恨。

“陛下……”奴才的声音再次响起,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,“北麓……已经平了。”
墨渊没有回头,依旧望着窗外那片被鲜血染红的天空。“烧了三天,够不够?”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。
“……足够了。”奴才的声音更低了。
“去告诉那些‘神选之人’,”墨渊的声音里重新染上冰冷的意味,“告诉他们,他们的神,回来了,只是,不再是他们想象中的模样。”
他站起身,缓步走下台阶,来到那具早已被血污浸透的御座前,他伸出手指,轻轻拂去龙椅扶手上凝固的暗红,动作近乎虔诚,又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扭曲。
“凡人……”他低声呢喃,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、扭曲的弧度,“终究只是凡人,连带着他们那点可笑的‘神恩’,也该被这双手,彻底埋葬。”
殿外,风起,卷起地上的灰烬与残肢,如同一场无声的葬礼,而这场由神明亲手导演的血腥,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相关文章:
文章已关闭评论!